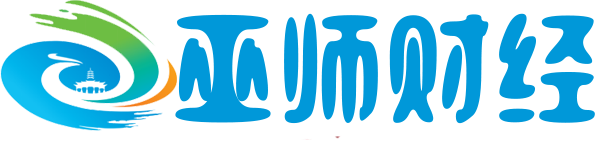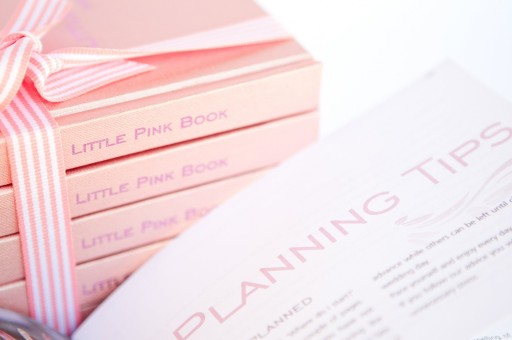风声|青少年犯罪越发频繁,究竟是父母之责,还是社会之病?
 摘要:
作者|陈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2025年6月27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表决通过,将于2026年1月1日...
摘要:
作者|陈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2025年6月27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表决通过,将于2026年1月1日... 作者|陈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2025年6月27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表决通过,将于2026年1月1日施行。在新法中,针对未成年人有诸多改动,包括调整行政拘留的执行条件、公安机关及时介入校园欺凌事件等,这回应了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上升且低龄化的问题,有部分情节严重的未成年人违法者未得到有效制约,“一味宽容”并不能起到未成年保护和犯罪预防的效果。
结合2024年最高检优化针对不满十四岁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核准追诉的态度来看,我国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治理方面,正朝着强化法律威慑力、完善法律体系衔接的方向调整。这给家庭敲响了警钟,倒逼家长强化监护职责,同时也给学校和社会提出了问题:究竟什么样的环境,才能从根源上防止未成年人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被网友称为今年截至目前最好的一部英剧《混沌少年时》,就讲述了一个13岁男孩杰米残忍杀害同学凯蒂的故事,揭示了青春期孩子的复杂世界和背后的社会问题。该剧的剧情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24年发生在邯郸的少年被害案——三名13岁的初一学生将同班同学骗到废弃的蔬菜大棚,其中一名手持铁锹将其杀害。警方只用了一天时间破案,最后两名主犯被判无期徒刑和十二年有期徒刑。时至今日,我们也只知道被害人疑似遭遇过校园霸凌,凶手和被害人都是留守儿童。至于他们为什么杀人,我们不得而知。
在这样的少年犯罪案件里,找出凶手实在是太容易了,因为他们太稚嫩,手法太不高明。所以,棘手的问题并不是找出谁干的,而是回答:少年为什么杀人?
我们在邯郸案里无法探求的真相,也许可以在《混沌少年时》里找到。
“少年之恶”从何而来?
这部剧集的英文名是Adolescence,直译为青春期。生物学家将青春期变化描述为,身体已经发育成熟,但大脑额叶皮层发育不足,情绪调节能力较弱,焦虑抑郁易怒等情绪频繁出现,缺乏自控,可能会做出一些冒险或不理智的决策。形象地说,成熟的外表下有着幼稚的头脑、汽车的发动机搭载着自行车的刹车。
电影《头脑特工队2》将其演绎为,进入青春期后,莫莉不再那么开心了,焦虑、嫉妒、尴尬、倦怠等新的情绪出现,尤其是焦虑占据了主导地位。她开始把朋友看得比家庭重要,和父母的互动减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学业和社交压力,差点崩溃。好在电影有个happy ending,莫莉幸运地度过了青春期的暗礁。但是,《混沌少年时》里的杰米没有。
实际上,他身上没有“问题少年”的那些刻板印象,比如父母离异、隔代抚养、家庭贫困。他的父亲是一名蓝领工人,母亲温和,姐姐友好,家庭条件不好不坏,而他学习也一直不差,看上去是个聪明乖巧、听话懂事的孩子。
凶案的导火索是这样的:同学凯蒂的裸照被人恶意传播,杰米觉得这是一个追求凯蒂的机会。但凯蒂拒绝并讽刺他:“我还不至于惨成这样”,还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反击他是Incel,意即“非自愿单身者”。很多同学点赞起哄,杰米的世界崩塌了。凯蒂本身是“黄暴”的受害者,她又转手伤害了杰米。而杰米的报复和攻击完全失控,在监控录像上看到,他残忍地用好友给他带来的刀捅死了凯蒂,捅了七刀之后,不动声色地回家睡觉。
剧中这帮孩子,个个都那么敏感,那么在乎外界的看法。无论男女,他们都特别害怕自己不受欢迎。男生要想受欢迎,就得仰仗外貌和阳刚程度,矮病弱丑穷都有可能成为嘲弄甚至霸凌的对象。而女生,可能是征服游戏的受益者,也可能不幸成为受害者。
剧中意味深长的一幕是,警察去学校调查案件时,调查对象一名初中男生问他,“你当年(读书的时候)很受欢迎吧?”因为警察看上去阳刚威猛,调查对象面露艳羡的表情。这意味着在他们眼里,征服女性就是这个年龄的王者。这也说明,同龄女性在他们眼里,既是皇冠又是猎物,既是条件又是障碍。
可惜,调查案件的警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理解不了男生们对征服女性的热衷,甚至都看不懂凯蒂对杰米社交媒体的反击,误以为二人是在友好互动——校园霸凌现在变得十分隐蔽,一些成年人看不懂的网络表情竟然是敌意的表达。
而校园里的老师也无法识别学生的心理危机,认为这就是叛逆期的正常表现。课堂上老师播放视频敷衍教学,学生对暴力事件围观拍摄,放肆叫好,这就是杰米和凯蒂所在的校园环境。他们都无法从周遭获得支持,获得对自己身份和价值的正确认知,他们拼命求生,但又绝望无助。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杰米在网暴漩涡中杀了凯蒂。其实,故事还有其他多种可能,比如,凯蒂因裸照事件陷入抑郁而自杀;杰米被孤立霸凌而自杀;学校爆出其他丑闻,杰米和凯蒂事件很快被遗忘……
我写这些,是想揭示一个惊人的真相:所谓少年之恶,可能并不是什么惊天大恶,凶案就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动机也许就和一个评价、一次互动有关。成年人过得去的坎,他们过不去。我们眼里的小事,就是他们的天崩地裂。
杰米的父母完全想象不到,13岁的杰米喜欢浏览色情网站、渴望脱单、渴望有异性的认可。他绝望得发疯,痛苦得发疯,才会酿成大祸。那么,在他们那么重要的时刻,父母在干什么呢?
孩子犯罪是不是父母的错?
其实,剧集一直都在拷问这个问题:孩子犯罪,是不是父母的错?故事从一个警察爸爸接到孩子的语音“爸爸,我今天能不去上学吗”开始,再到杰米的爸爸最后把脸埋进枕头无声哭泣“对不起,儿子”结束,一种巨大的压抑和绝望感弥漫在空气里。
剧集中的两个爸爸,让人印象深刻。警察爸爸回避和孩子的沟通,认为孩子不想上学的事情找妈妈就能解决。结果他去学校调查凶案才知道,他儿子不愿上学,其实是因为在学校受到严重霸凌,同学嘲笑他长得丑,向他的餐盘中扔垃圾。而老师们,几乎熟视无睹。
杰米的爸爸同样不知道杰米在学校被人吐口水,不招人待见。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好父亲,因为曾经有过被家暴的童年,所以他发誓绝对不打孩子。他辛苦工作,对家庭忠诚,省钱给儿子买了电脑。他以为儿子整天窝在房间里,怎么可能学坏呢?殊不知,那个小小的电脑或者手机屏幕能连接到整个世界,带来无法预料的伤害。
悲剧的是,青春期的孩子那么敏感,而父母却对青春期的孩子一无所知。父母对儿子变成杀人犯这件事感到悲苦,完全没想到儿子才13岁竟然迷恋女性和色情,还有Incel的烦恼。成年人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孩子,孩子们则完全不信任成年人,他们使用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像活在两个平行的宇宙里。
警察爸爸在校园调查之后终于意识到了什么,他主动邀请儿子“吃个薯条”一起聊聊,儿子难以置信而又带着期待,还好他们还是一起去了。而杰米的爸爸,终于成了那个最后知道真相的人。也许是他工作占用了太多时间,和孩子的沟通不够;也许是他对孩子各方面资质平平的失望,让杰米感到自己无法获得权威的认可;最后他们越行越远,可明明都是彼此最在乎的人。
看到这里,也许有很多中国父母也共情了:到底该如何对待孩子,打还是不打?爱要怎么爱?要怎么陪伴?怎么做才不会错?
和《混沌少年时》一样,中国的父亲也不了解自己的孩子,在子女的生活中像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他们可能卖力工作,可能在外边忙忙碌碌,但在儿女面前都是那样沉默拘谨。李宗盛有一首歌叫《新写的旧歌》,他用这首歌和去世的父亲和解了:“两个男人极有可能终其一生只是长得像,有幸运的成为知己,有不幸的只能是甲乙。”
就像杰米爸爸说的那样,“我发誓我绝不打我的孩子”,他做到了。但是,如果两个人一生“只是甲乙”也就罢了;如果你错失了挽救他的机会,对他的罪错一无所知,眼见他掉进深渊里却不能拉一把,该是怎样痛彻心扉。
杰米的父亲自认尽到了责任,但任何人都受限于他的人生经验。他传统保守,性格有缺陷,情绪也会失控,有时沉默不善表达。这不就是普通年代的普通人吗?把杰米犯罪的原因归咎于父亲关爱的缺失,同样也是残忍的。
《混沌少年时》中的孩子父母,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但时代变了,他们被裹挟其中,茫然无知,他们未曾经历的、不能理解的冲突,成为他们与孩子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当上一代人的经验无法为下一代做出指引的时候,少年就转向互联网,寻找新的偶像。可惜他们找到的偶像,竟然是安德里泰特这样的厌女网红。
霸凌或犯罪,是不是社会病了?
该剧还展示了社交网络如何成为未成年人霸凌的工具。未成年人通过手机和电脑屏幕连接到整个世界,这是最好的时代;但也意味着他们无法逃避网络上的恶意和欺凌,这又是最坏的时代。
网暴的威力,我们实在太熟悉了。刘学州寻亲被网暴案,就是典型的发生在未成年人身上的网暴遭遇。2022年1月24日,他因遭遇网络暴力在海南三亚海边服药自尽,年仅16岁。网暴的破坏力,会层层加码:隐私照片和信息在短时间内让大量用户看到,会造成社会性死亡;恶意者还可以利用评论、私信等功能对受害者进行言语攻击,让人陷入恐惧和自我怀疑;如果恶化,受害者被群体孤立和排斥,还可能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陷入抑郁,甚至自杀。
由于血泪教训太多,我国近年来通过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除此之外,还在两高一部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中特别规定,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网络暴力的从重处罚。尽管如此,网络暴力的隐蔽性、传播快等特点,仍使得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暴力频繁发生。
更让人震惊的是,小孩也会变成加害者,利用网络曝光他人隐私,比如今年3月引发关注的国内某大厂高管13岁的女儿多次“开盒”素人。这说明,暴力和不良行为具有习得性,尤其在网络上,匿名性和低门槛为冲动少年提供了宣泄负面情绪的“安全出口”。
在《混沌少年时》中,不管是在凯蒂还是杰米身上,我们都能看到社交网络对他们的同等伤害。他们霸凌别人,也被人霸凌。只不过,他们学到了黑暗丛林里不同的生存技巧。凯蒂在社交平台上伤害了杰米,而杰米选择了在现实生活中进行杀戮。
但凯蒂的那些留言,只是一个被害者的慌不择言和应激反抗罢了。她在荡妇羞辱和网络霸凌中学到的,跟“正面连接”报道的故事《从家中偷走一个11岁女孩》一样——郑州一个11岁的女孩被朋友诱骗,多次被性侵,后被骗入卖淫团伙,最后参与对他人的施暴。就暴力而言,她学到的是,“人只要看上去软弱,谁都可以来踩一脚。”
剧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在于,揭示了社交媒体中的厌女理论。杰米的杀人动机,来自女性对其自尊的摧毁和社交媒体中的厌女理论的影响。鼓吹厌女理论影响力最大者,就是著名网红安德鲁泰特。这个人是一个绝对的性别歧视者,鼓吹真理掌握在最少数的男性手中以及“二八法则”,意思是80%的女性会追求20%的优秀男性,剩下的男人都会成为“非自愿单身者”。如果男性想找到性伴侣,就必须对女性采取情感操纵手段。在他看来,女性贪慕虚荣,择强而栖;与此同时,又暗示男性群体里的失败者应该去怪女性,失败者都不值得同情。
最近,“大同订婚强奸案”的网络喧嚣中出现了明显的厌女情绪,判决本想表达的核心要义是“订婚不等于性同意”;而部分网友在讨论的时候,将之与此前出现的一些男方支付了高额彩礼而女方悔婚的民事案件相关联,认为女方是情感欺诈。这种情绪,也体现在一款流行游戏《捞女游戏》中(已更名为《情感反诈模拟器》),该游戏得到了很多男性玩家的追捧,在内置的留言板里就充斥着大量厌女言论,把情感诈骗归结为女性的问题,加剧了性别对立和偏见。
厌女是一种危险的情绪,这将带来一系列针对女性的污名和暴力。而标记他人Incel这个行为,本身也有两面性。如果只是客观描述单身状态,那没有恶意。但毫无同理心地对他人进行冷嘲热讽,或者带着刻板印象,认为只有符合某种标准的人才有资格幸福,那也同样中了厌女理论的毒。这也说明,厌女的,并不只有男性;女性的慕强也可能会被放大,强化对女性的负面看法,进而导致厌女。
这是成年人世界里的厌女,它也影响了未成年人。有报道援引英国教育大臣的话,假如我们不加警惕,努力了一个世纪的性别平等就可能倾覆,这也正是这部英剧值得每个人深思的地方。女性是厌女理论的受害者,而男性也同样可能被压抑和固化。如受害者看不到结构问题,他们会互害。剧烈的性别对立之下,最终屠刀指向的就是那些最弱的人。
重估少年犯罪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混沌少年时》为我们展现了未成年人犯罪背后复杂而深重的社会议题:这是一部克制仇恨、避免偏见而致力于反思的剧集,它既没有渲染凶手天生的恶,也没有放大被害人的问题,它只是冷静地观察,抽丝剥茧,让你自己看到真相、找到答案。
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以往讨论我国的未成年人罪错的时候,往往局限于刑事责任年龄以及少年的权利,局限于个案的正义。这部剧告诉我们,这样的关注远远不够,刑事追诉和治安处罚只是一个小切面。我们中国的混沌少年,棘手的可能不是厌女问题,但我们有单一的教育评价体系,有成瘾的社交网络,有时代的留守儿童,也有失控的网络暴力。我们的孩子,也并不安全。
如果导致少年犯罪的,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呢?如果是社会病了呢?如果是父母这一代根本没有能力给青少年提供应有的支持呢?我们的孩子承担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没有任何过来人可以向他们讲述经验。这个时候,责怪孩子或者父母可能都是不明智的。
我们需要关注个案中养育那些霸凌者的文化土壤是什么,如果孩子的某些罪错行为,恰恰是想让自己符合某一类被认可和追捧的文化标准,那么,整个社会都应该深刻反思并行动起来,该警惕的是那些宣扬倚强凌弱、强者通吃的有毒思想。
我们要做的,是以更包容的姿态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让孩子无需扭曲自我,无需认同强者,也能在健康的文化环境里找到自己的坐标。
在《混沌少年时》的最后一刻,杰米终于能够直面自己的行为,从之前一直逃避不肯承认自己杀人,到最后他给父母打电话说,“我想认罪了。”父亲沉默了很久很久,独自走进儿子的房间。他抱着儿子的小熊,流着泪说,“对不起儿子,爸爸可以做得更好。”这一幕,相当动人。
无论是荧屏还是现实,都提示我们重估少年犯罪预防和控制的紧迫性与必要性。这对家庭而言,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法治理想国”由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赵宏、李红勃、罗翔共同发起,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栏目。
主编 | 萧轶